gpt 文爱 独家专访香港金牌编剧杜国威:粤剧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竹林七贤,我来试一试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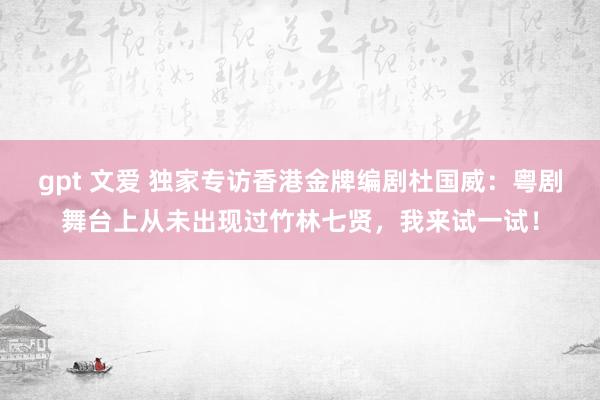
10月17日晚gpt 文爱,香港金牌编剧杜国威的新编粤剧《竹林爱传奇》登上广州大剧院的舞台,这是该剧在内地的首场献技。

《竹林爱传奇》取材自魏末晋初“竹林七贤”的职业,论述七贤后东说念主向冲和嵇旦的爱情传奇。一双年青爱侣在盘曲阅历中罢了父辈遗志,并玉成我方的生命追求。故事情节环环相扣,高涨迭起。
献技甘休后,杜国威上台鞠躬致谢,引得不雅众起身献出如雷掌声。
在不久前的共享会上,已年过古稀的杜国威想路了了,语速极快,讲到兴起时欢蹦乱跳,颇似新剧里的武打小生,有绝世武功却游戏东说念主生。
“面前作念任何事只忠于我方,不策动所谓的收获。多一个年青东说念主看粤剧,就多一份传承。”他坦率说说念。
在专访中,杜国威告诉记者,他打小就和粤剧结下不明之缘,年事小小的他就参加“丽的呼声”电视台,以童星播音员身份与洗剑丽、邓寄尘等名伶搭档献技。“咱们那一代东说念主,看大戏就如面前的小一又友神话唱一样稀松宽广,进戏院后坐在母亲膝上即是一晚了。”
尽管早年已创作过《虎度门》《珍珠衫》《南海十三郎》等以粤剧为题材的舞台剧,但他一直想写出一部“真确”的粤剧,锣饱读、板腔、作念手样样皆有,终而写就竹林间的热血爱情故事。

1、“作念大戏”很少有这样多男主角
羊城晚报:您的粤剧新作《竹林爱传奇》灵感源于那里?为何聚焦竹林七贤后东说念主的故事?
杜国威:这部剧是我在2023年头构想的,和之前创作的粤剧《珍珠衫》不同,我但愿此次不错聚焦古代东说念主物,野心小生和旦角的变装,于是梳理了各朝代的故事。
其中最容易入辖下手的应该是明清时期,不错引入汉代、唐代和宋代的诗词歌赋,但这些朝代中已稀有不清的、众所周知的粤剧东说念主物形象,比如书生、将军,对我来说穷乏了挑战感。自后我发现,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虽广为东说念主知,但从未出面前粤剧戏台上,我想试一试。

竹林七贤里有七个男性变装,“作念大戏”很少有这样多的东说念主物,何况全是男性。与其写魏晋时期的“好意思男天团”,倒不如研讨下他们之间有哪些趣事不错在剧中打发,不错发达编剧的假想力,去构建一个全新的魏晋传奇故事。这亦然我把创作布景蔓延到竹林七贤后代身上,去写他们子女的境况、对爱情的追求的原因。
羊城晚报:神话《竹林爱传奇》是您为了蓝天助、郑雅琪这对“郎才女貌”量身定作念的脚本?
杜国威:还简直是,这还得从一段缘开动提及。那天他们在元朗的一家市场里吃饭,刚好聊起我,雅琪说,淌若我能为她写一部戏就好了。
我那时正在那家市场漫无方针地闲荡,又碰劲从他们死后走过,被雅琪看到了。就像天意一样,他们拉着我坐下聊天,我也就有了为他们写一部剧的念头。
其实咱们不是惟一那“一面之缘”,之前就有过互助。在粤剧《珍珠衫》里,那时“阿蓝”(蓝天助)年事还很小,他扮相潇洒、武打塌实,很有不雅众缘。雅琪之前演了好多唐涤生的戏,像《紫钗记》《帝女花》那些经典剧目她皆能演好,是一个唱腔和声嗓俱佳的旦角。
天助和雅琪他们这群粤剧少壮很肃穆、很勤劳,这种气派打动了我。我再行看过他们的作品,去了解他们面前的戏路,构想相宜他们定位的变装。除了分缘,他们也为我方争取了契机。
2、多一个年青东说念主看粤剧,就多一份承传
羊城晚报:对您来说,本次新剧创作的难点体面前哪些方面?
杜国威:“竹林七贤”在体裁上的成即是很伟大的,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皆谨记他们的诗词歌赋,同期也有玄门的想想,在咱们中国东说念主的传统文化里,一直离不开“儒释说念”文化的影响,培养了中国东说念主光明方正的说念德不雅。
然而把它们改编成戏曲,就要研讨戏剧冲击和戏剧元素,改编成既有历史又有爱恨分明的脚本是很繁难的,需要很丰富的假想力。
如果你看了这部戏,问我哪一段是简直,哪一段是假的,事实上有可能简直是假的、假的是简直,这即是戏剧的道理性。比如戏里的《广陵散》一段,假如再果敢少许,能不行整部戏皆是嵇康和阿谁阴魂的戏?因为靠你的假想力,这个不难,阴魂没东说念主知说念是如何样,何况咱们皆抵抗气有鬼,你如何写皆不错。
我以为东说念主物应该为了故事而职业,不要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尝试。我写脚本写了四十多年,不错说越写越不怕失败,因为我以为东说念主不会每样皆这样收效。
在《我和春天有个约聚》广受接待的时候,如果我怕口碑变差,就不会敢写《南海十三郎》。生命是一条很长的路,你不会恒久在岑岭,一定有低位,要想考的是如何靠近。
羊城晚报:《竹林爱传奇》在广州大剧院的首演,眩惑了好多没看过粤剧的年青东说念主进场,您认为这部粤剧取得年青东说念主青睐的原因是什么?
杜国威:《竹林爱传奇》在传承的同期又有鼎新。他们心爱说“新编”“新派”,我我方不会讲这些意见,咱们不是为了新而烧毁了旧,而是尽量作念一个传承加创意的完满组合。
黑丝av鼎新基于传统,粤剧非论如何变化皆有独有的魔力。锣饱读“咚咚锵”,唢呐“的禾的禾”,以至演员还没出声,大家就知说念在“作念大戏”。拉腔的“问字攞腔”,粤语的声韵格律,换一种音调或者方言就透彻“变味”了。多一个东说念主看粤剧,咱们就多一份承传。

同期粤剧在束缚地变化出新。比如曾小敏在《白蛇传·情》里用一段广东音乐来论述白蛇、许仙的相见,她野心了此前没见过的身体、姿态,来展现见到情郎的憨涩和惊喜,而传统《白蛇传》仅仅用锣饱读、甩水袖来掩藏。再比如你有听过大戏唱duet(二重唱)吗?《竹林爱传奇》里就有。
面前不少年青东说念主以为粤剧很冗长、很败兴,不是这样的,粤剧少许也不Out(落后)。我这辈子最怕被别东说念主说我写的戏很闷。省心,不会闷的,我会在你想哭的时候让你笑,一两句台词你就会笑。
3、我缓缓开动写“不那么仁爱的东说念主”
羊城晚报:好多戏迷在谈到您的作品时,率先料想的即是一个“情”字,您如何意会关于“情”的阐释?
杜国威:“情”很蹙迫。我通过戏剧来讲东说念主性,东说念主性里很容易流败露情愫。能够让不雅众产生共识的变装,他一定有很精细的情愫。
我年青时不心爱写“衰东说念主”(粤语:坏东说念主),我以为不同的情愫故事不错让不雅众情至意尽、难忘于心。和电影一样,舞台剧的职责亦然加强东说念主与东说念主之间的一样,我不心爱品评别东说念主,倾向于展现东说念主性好意思好的一面。
直到这些年,我才缓缓开动写“不那么仁爱的东说念主”,因为我想告诉大家,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你身边的东说念主,才会更了解他们。面前的我,不怕去更潜入地探讨东说念主性。多情愫的东说念主想想会变得复杂,从而产生许多矛盾,写脚本即是通过故事探讨这些矛盾。
期间在变化,咱们的作品也在变化,坏东说念主不是浅显地贴上“杀父仇东说念主”“渣男”的标签就能综合的。“坏到底”的变装频频让东说念主以为区别理、很稚子。编剧需要用故事和不雅众产生共识,用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故事才会跃然纸上。
羊城晚报:会不会有“入戏太深”放不下的时候?
杜国威:好多东说念主问过我,我写南海十三郎是不是在写我方?我每次皆说,诚然不是,我好容易为五斗米垂头的(笑)。如果每个剧的变装皆像我方,那是“吊问”,是写得不好。
我写的好多脚本皆从庸东说念主物的角度开赴,因为我民风了从小到普遍以理性、东说念主性的角度去看待事物,而这一角度恰是千古以来东说念主类从未脱离过的。
在写《南海十三郎》之前,我没想过白话化的脚本也不错成为“体裁经典”,不雅众通过舞台剧、电影等影像作品去看到脚本之外的寰宇,这是很高的体裁意境。《南海十三郎》写出了曩昔某些本领香港东说念主怀道迷邦的心声,十三郎就算是失败的时候,他仍然不怕失败、果敢尝试,这种精神荧惑着咱们。
脚本不是光靠想出来的,想写好一个脚本要采访好多东说念主、作念好多考证。如果你莫得切身战争,就很难写出有深度、跃然纸上的东说念主物,以至要将我方代入进去,感受他们的情态,改革为剧中的变装,让变装与变装之间交流。
我询查东说念主,一辈子皆不以为闷。以至我无用看东说念主,我只须听声息就能好像猜到,这个东说念主是什么样的,他的脾气如何样,最近开不得意、为了什么而得意。我以为这是天赐予我的编剧才智,是以在写稿的时候,我反而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嗅觉。
4、忠于我方是东说念主生最大的原能源
羊城晚报:您曾先容我方处于“半退休”状况,如今的创作节律如何?除了写稿,日常生存中还有哪些风趣爱好?
杜国威:我写脚本写了四十多年,写过的电影脚本、舞台脚本琳琅满目过百部,偶然以为我方写不动了(笑)。面前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才有精神,每写完一部脚本皆要歇很长一段时候,等我方有风趣再想第二部。
除了写稿,我面前的风趣即是画中国画。其实我十几岁时就学过水墨画,旧年底出书了《杜国威水墨作品(第二册)》,其中收录了我近几年来画的十几幅画。我用了四年时候重拾画笔,挑升租下一间货仓房间创作五尺乘以四尺的国画,部分作品也曾去到新加坡参展。

画画和写稿是两个寰宇。我手画我心,我心爱加什么元素皆不错,笔画的高下、粗细、浓淡皆由我方决定,莫得电影、舞台、监制、导演和演员傍边我的想维。
若果要比拟,只可说面前的我每天皆比前一天更甘心,一杯茶、一个猪仔包就不错很enjoy(享受)。忠于我方,是我现今东说念主生最大的原能源。

羊城晚报:如何再选用一次,您还会当编剧吗?
杜国威:我从6岁开动演播音剧,情愫故事、大东说念主讲的台词演多了,就知说念何谓人情冷暖,见到很厚情面世故,懂得写脚本。13岁那年,我因为变声告别文娱圈,作念回一个粗俗学生,那时以为生存很不如意,不错说躲在我方挖的岩穴里。
那时我莫得东说念主生方针,也不心爱读地舆,整天在惦念,教悔的英文一句皆听不懂。自后毕业作念地舆憨厚,我以为如果连我我方皆躲起来,如何靠近我的学生?那时可立中学校长的老婆是我的中学憨厚,她知说念我小时候作念过播音,就请我搞课外行径,办“可立剧社”。
重遇戏剧后,我才再行找到甘心。那一幕寥若晨星在目,作念完《昨天孩子》那场戏后,一群话剧发热友走来和我捏手,泪如雨下,原本戏剧不错这样有感染力。我十三岁之后的情愫压抑,像个气球一爆不可打理。戏剧让我从我方的狭窄寰宇里走出来望望别东说念主,不要把我方的问题看得那么蹙迫,不要以为很细小,也不要以为我方很蹙迫。
那时有三条路(播音东说念主、锻练、编剧)不错走,但我选用了编剧这条路,这即是我的气运。我不想重新再来,但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得意,我面前即是最得意的。
羊城晚报:《南海十三郎》中那句“一个好的脚本,50年、100年后仍会有东说念主抚玩”,激发了若干后生编剧!关于新入行的年青东说念主,您想对他们提议哪些建议?
杜国威:我时常跟年青东说念主说,我在38岁那年才“开窍”。这个起步点的公道是那时我的写稿照旧比拟老到,坏处是我莫得试错的时候,不行重新再来,唯有像个“傻佬”那样束缚地测验,练到“百毒不侵”。
面前入行的年青东说念主,他们的动机更贞洁,以前一班“涎水佬”坐在总计brainstorming(集想广益)就能营生,可能根柢没写出好的本色。面前的年青编剧明知说念“没钱赚”仍景象为了趣味而入行,我很感动也很谢忱。但愿他们能够打好基础,让我方更有才智和讲话权,争取更大的创作空间。
文|记者 梁善茵 黄宙辉 实习生 朱心怡 图|广州大剧院 部分由受访者提供gpt 文爱
